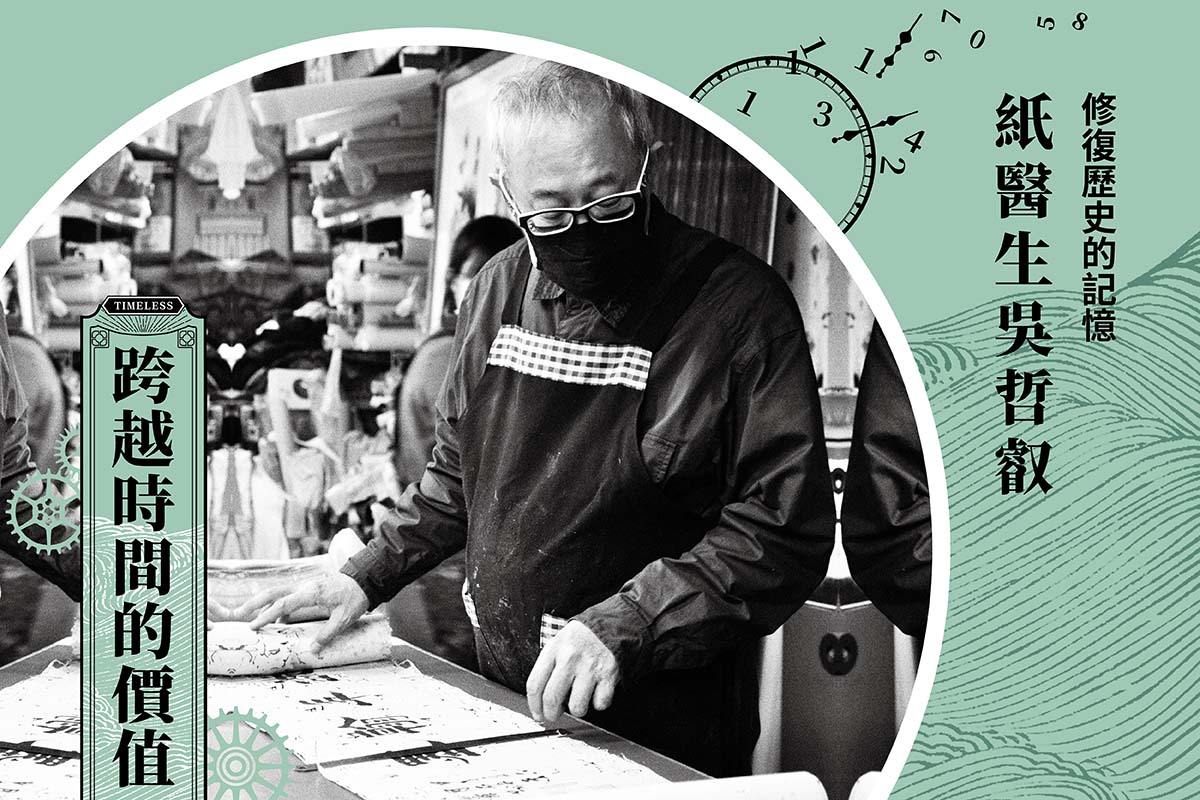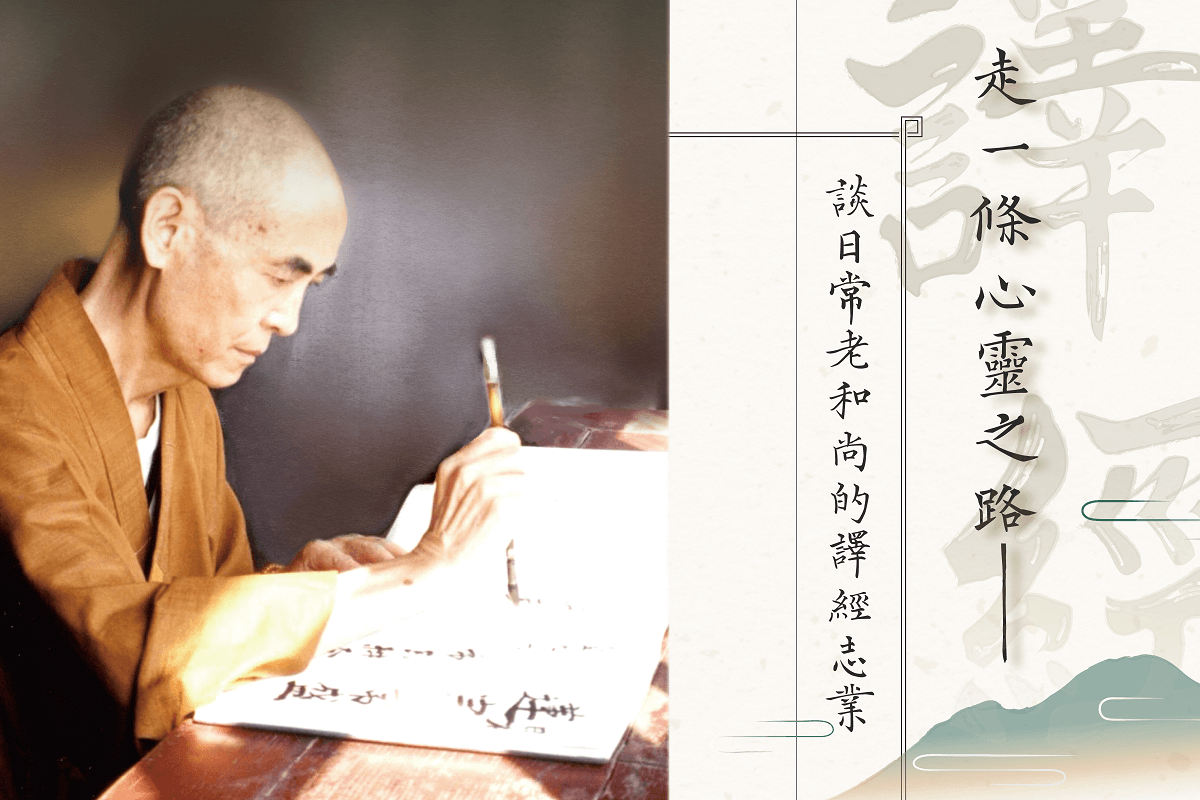關於訪客,有一個有趣的故事:一個主人希望家裡的訪客趕快離開,就在牆壁上寫了一首詩:「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」。沒想到匆忙中忘了標點,客人就將他的詩擅改為「下雨天,留客天!天留我不?留」,毫不客氣地留下來了。
這種賴皮的訪客畢竟少之又少,只是一個趣味笑談而已。其實植物界也有主人與外來訪客的區別,分別稱為「原生種」與「外來種」。植物種子的傳播,原本是靠大自然的力量,風吹水流、鳥禽走獸散播。而真正長距離地遷徙,當是在人力介入後,人類有了汽車、輪船、甚至飛機,能將南美洲的植物移往北半球,而遠離了故土的植株如適應當地的氣候、土壤存活,在異鄉落地生根,為當地增添新的植株生態,應該也是美事一件,因為物種越多元,能提供的食物、棲地就越多樣,物種的生存繁衍就愈加蓬勃豐富。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中通過的「生物多樣性公約」,就是一條關於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國際性條約,希望所有物種都能共享這個星球的資源,讓地球的生態更豐富,更平衡。
以寶島台灣為例,由於缺乏正式的文獻,台灣原生種植物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記載,隋書中描述「流求國」的耕作:「土宜稻、梁、黍、麻豆、赤豆、胡豆、黑豆等」,晚明陳第「東番記」中亦有記載:「穀有大小豆,有胡麻,又有薏仁,食之已瘴癘;無麥。蔬有蔥,有薑,有番薯,有蹲鴟(大芋);無他菜。菓有椰,有毛柿,有佛手柑,有甘蔗。」,由這些記載可知是當時既有的作物。
寶島外來種的引入正如台灣通史序中「荷人啟之,鄭氏作之,清代營之」的順序:「番茄、番石榴、番荔枝(釋迦)等」被冠番字是當時對荷蘭人的標記,而豌豆則直接命名為「荷蘭豆」了;明鄭時期則是以華南一代桃李梅、蔥韭等故鄉風物及玉蘭、樹蘭、含笑等香花為主,一解唐山過台灣思鄉之情,桑樹、烏臼等也是此時來台;到了清代,荔枝龍眼文旦楊桃等水果,桂花仙丹等花卉亦由華南一代陸續入台;日治時期則是外來種最頻繁引入的時期,對地處溫帶的日本而言,亞熱帶的台灣充滿異國風情,當時的殖民者在島內廣植椰子、棕櫚、蒲葵等,並大量引進經濟作物如油桐,瓊麻等,大大改變了台灣的地景樣貌及生活狀態。民國之後外來物種的拜訪更加多樣,使得島內林相生態更加豐富多元 。
雖然絕大多數原生種植株和外來種都能分享棲地、和平共存,但仍有少數物種入得門後喧賓奪主,直接擠壓原有物種的生存空間,這種侵門踏戶甚至「乞丐趕廟公」的失控訪客,國際自然保育聯盟(IUCN)定義為「外來入侵種」,認為會「促成改變,而威脅到當地的生物多樣性」。外來入侵種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原本棲地植株的存亡,也將促使所有賴此植株棲身、覓食的生物面臨滅絕的危機,間接造成林相單調、物種貧乏的不良後果。
台灣少數被列為外來入侵種的植株中,有些物種初來乍到時,其實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,但因時空環境改變,反倒成為生態負擔。如早在荷蘭時期就引進台灣做為薪材及動物飼料的銀合歡,在原本功能喪失後,頓時從明星樹種成為生態惡夢。「澎湖銀合歡」歇後語「眾人剉」,就是眾人咒罵、唾棄的意思。澎湖風大土地貧瘠,欠缺林木薪材,煮食只能以牛糞曬乾為燃料,引進銀合歡解決當地燃料不足的危機,當時可說是大受歡迎,怎知物換星移,當煮飯不必砍材時,銀合歡的地位一落千丈,無人聞問,就在野地恣意生長、蔓延,成為澎湖生態環境永遠的傷痛。
而日治時期因花形姣好而被引進觀花的布袋蓮,美則美矣,因生長快速,容易遮蔽河面,阻礙了水中生物的生長,且常堵塞出水口造成水質惡化,也是當今亟待移除的入侵種之一。另為島內冬日蜜源而大肆廣植的大花咸豐草,就如同它的別名「恰查某」般,一女當關,萬草莫敵,迅速在野地蔓延,且因種子上有倒勾,可攀附人類衣服褲腳隨處散播,強勢威脅野地花草的生存空間,雖能緩解寶島冬日花卉鮮少、蜜源不足的問題,但其嚴重擠壓野地多元生態已到必須外力介入的程度了。
銀合歡、布袋蓮、大花咸豐草等雖衍生為生態負擔,然對人類生活尚不致於有立即威脅,造成迫切危機的當屬有「綠癌」之稱的「小花蔓澤蘭」,它於何時何因引進寶島眾說紛紜,只能確定民國七十五年就在屏東出現,數十年間已成山林噩夢,由它的別名「一分鐘一英里草(Mile-a-minute weed)」可知其成長的迅速,據說在花季期間,每平方公尺可產出高達十七萬顆種子,而種子輕薄,隨風飄颺,根莖的節與節之間還能長出「不定根」無性繁殖,在野地恣意蔓延,不僅纏勒植株、覆蓋樹頂,使植物無法行光合作用而枯萎,寄生此植株或以此覓食的生物也會因而瀕臨滅絕,更有甚者,大樹倒下只留藤蔓橫行,原有的固土、水保功能消失,土石流之災當更頻繁,說是生態浩劫實不為過啊!
小花蔓澤蘭的樹葉類似長版心形,葉子尾端細長如小尾巴,上方有兩片對稱突出,類似狐狸形狀,開小白花,外形可愛,不易起戒心,但若令其隨意生長,不僅影響山林野地多元物種生存,更可能直接威脅人類生命財產安全,所以亟需政府民間攜手合作全力移除。
移除小花蔓澤蘭的最佳時機是每年九月十月開花之前,移除時可直接用手折斷,如藤蔓已落地生根需將樹底莖部切斷,離地至少二十公分,以確保其無法接觸土壤再次萌發。移除後的藤蔓當直接放入堅固的塑膠袋中,捆緊袋口再行丟棄,千萬不可堆置一旁任其枯萎,只要種子還在,隨風飛揚落入土中又會萌發新的植株,「野火燒不盡,春風吹又生」它的生命力就是如此頑強堅韌,所以除惡務盡,不可輕忽。
面對生態危機,身為地球村成員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,除了配合政府民間的各項活動盡一己之力外,來往國際的旅人亦當謹守生態公約,不隨意攜帶外來種子入境,以免不經意中引進未經評估過的物種,衍生生態問題。「環保護生愛地球」絕非口號,需要全民共識與行動才能確保地球的永續經營。
安泊
教職退休的後中年女子。
喜閱讀、嗜電影,悠遊文字影像之間,樂此不疲。
走步道、愛旅行,用雙腳走山林,親近鳥獸草木、山川風物,自覺不老。